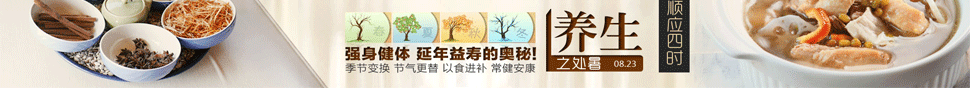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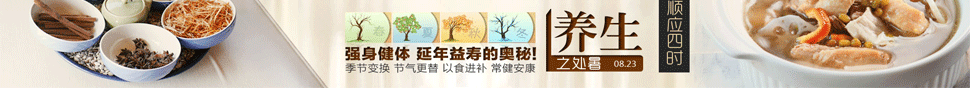
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总第期编发:元辰
吴绪久,男,枝江市人。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宜昌三峡人文研究所所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内蒙)专家委员,湖北省作协会员,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宜昌市屈原学会副主席。历任宜昌市作协、三峡诗词学会、屈原诗词学会副主席,《天然塔》文艺主编。出版《走进三峡》《大三峡的儿子》《九久诗稿》《吴绪久三峡咏稿》《洒爱大渡河》《亲言且絮语》等文学专著多部,发表各类文艺作品数百万字。主编《大学实用写作》,被教育部审定为“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主编《写意大三峡》、《紫叶集》多部散文集。散文《车辙》、《最是三峡极顶处》、《三峡橙子红》等相继被选为大学、中学教材。荣获湖北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宜昌市委宣传部第五届屈原文学奖特别奖、宜昌市文联年度优秀成果奖、《中国作家》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世纪“共和国之歌”大型征文一等奖、宜昌市委宣传部年度精品文艺项目扶持奖。
吴绪久散文四章
野藜自是故乡来
刚才,也就是年元月19日下午三点时,看了一段视频,是讲乡愁的,讲一代人的乡愁,讲得很感人,是一位女作家的演讲,竟有不少人听后流泪了。是的,乡愁是我们每个人永远的思念。只要故土在,乡愁就在,只要流水在,乡愁就在,只要故乡的风物在,乡愁就在,也只要我的思念还在,乡愁就在。
我的前院里,野藜蒿根发芽了,让我的乡愁又发芽了。我们的老家是在沮漳河边。那河边是有许多野菜的,野藜蒿,野荠菜,还有苜蓿,这些,在灾年时,它填饱了我们的肚子,帮我们渡过了那困难的岁月。而温饱之后,它又成了我们舌尖上的美味。尤其是野藜蒿,它竟成为了我们的最爱。好多年前,我便写过一则短文,是专门讲家乡那野藜蒿的。在文中,我还讲到这样一件事,年春,嘿,距今竟然50多年了,我们高中的同学,响应当时“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决定到国营草埠湖农场去,边劳动,边上课。从宜昌到这农场,得先坐船到枝江的江口镇,然后步行,这样就得路过我的家,其时,天已晚了,便在我们家打住下来。那天,母亲就特地去采了些野藜蒿,做了一大碗,来款待这些请都请不来的客人。同学们吃了这菜,都觉得好香呀!好香呀!由于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山区和丘陵地区来的,他们那儿是不长这些野藜蒿的。野藜蒿是我们这小河奉献给我们的特有礼物,所以,一些同学很好奇,总是不断地追问着它的名字和性能,以至于二十多年后同学相逢,大家还在念念不忘地对我说,那年,你母亲做的野藜蒿真好吃,后来总是想吃到它,可一直就没见着。虽然后来市面上有了,但总找不出那美味的感觉。
是的,野藜蒿好吃,这是不假的,它浸润着小河的清乳,吸吮肴沙坡的松软,纯天然,纯有机,还有什么比它更绿色呢?而且,我家乡的小河边,那野藜蒿总是长得尤其丰茂,一丛丛,一片片,绿里透红的茎,粉里透绿的叶,尖尖的茎,尖尖的叶,很让人喜爱。在我的记忆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还有人驾着小船来我们这河边割走一船一船的野藜蒿,偷偷的运到荆州和沙市去售卖。当时让我很是惊异,这些人真大胆,竟然不怕把他们给“割”了!可见出那美味的力量了!
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但这种乡愁是愈久愈盛的。在家乡,关于野藜蒿曾有些谚语,有句就是这样说的,“正月的藜,二月的蒿,三月四月当柴烧”。可以看出,它是一道时令菜,正月采吃是美味的最佳了。记得我还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对这种乡愁的记怀:“春风先破柳芽开,夜雨清风习习来。脚板沾泥人嬉闹,趁晨采满藜蒿苔。”就是写春天到了,孩子们去河边采藜蒿的情景。那种欢快,那种喜悦,现在想来,仍让人留恋和沉缅呀!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那两年,我的父母亲相继过世后,都安眠在故土。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回乡祭奠。插青完毕后,总得弯到河边去采一些野藜蒿的。大概是年吧,小河边的野藜蒿是出奇的茂盛。我们几姊妹,老伴她们几妯娌,采了好多好多呀!老伴和妹妹她们还在河边的小亭子里把这些野藜蒿都一根一根剔净,整理好,然后带回了枝江,好好地炒了几大盘,大家美美地享受了一餐,自然,这是在享受着乡愁。没有炒完的,弟弟妹妹他们硬要我老伴带回了宜昌,让我们继续去享受这妙不可言的美味,这满是春情的乡愁啊……的确,这种乡愁是浓郁的,只有游子才能品味的,也只有我们才能拥有呀!
今天,我骤然看见门前沙堆里野藜蒿发芽了,它是带着乡愁发芽的!这些野藜蒿根是前两天,家乡的侄子俊平和美明他们特地在小河边挖后送来的,真的,当时我不在家,他们便把这些野藜蒿掩进了沙堆里,并打电话对我说,要不了几天,这些野藜蒿就会发芽了。真的,今天发芽了!细细的芽叶已从沙堆里钻了出来,淡淡的绿,浅浅的芯,似乎在向我讲述着往事,讲述着那些难以忘却的思念。是啊,他们送来的,决不仅仅是一些野藜蒿啊!这是乡愁,这是乡情!这也是亲情呀!这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
野藜蒿发芽了。它是带着乡愁发芽的,是带着亲情发芽的!明天就是大寒了,它标志着冬天即要离去,春天马上就要来到,这时,谁能不相信,这些野藜蒿不会滋滋地生长!是的,一定是的,这些野藜蒿必定会把浓浓的乡愁送达于心的!
是啊,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必将在春风中继续抽长着……
野藜自是故乡来,
芽沐舂风淡淡开。
愁绪植根沙土里,
一日三秋总入怀。
一一不尽的乡愁,不尽的眷恋
(年元月19日下午于宜昌半岭居)
土土的乡情
五月一日,劳动节,不少朋友都利用这个机会,去了名山大川,去了名都古镇,去感受美景带来的愉悦,去感受大厦带来的震憾。而我却是去了一趟乡下,去看望了仍在劳动着的妻兄妻弟和妻妹们。
当年,我们都曾在乡下,那时我们也都还年轻,往来也多。后来,恢复高考我即离开农村,便从乡下来到了宜昌这个城市。路远了,走动就相对少了些。岁月如流水,一晃我们都已老了,连最小的舅弟也快花甲了。前些年我的妻子在世时,春天或者秋天,她总会到乡下玩上些日子的。她们几姊妹的感情是不错的。我这次去,也是代我天堂的老伴去看望看望他们。
舅兄听说我要来,也是忙前忙后的,忙着。并把舅弟和两个姨妹夫妇都邀到他这儿来了。让我能和大家都见见面,都能好好叙叙。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都成了留守“老人”。但他们的生活过得都还惬意。舅兄已经是早过古稀,但身板还硬朗,两个儿子都在外拼闯,屋里的田他还一个人揽着。嫂子在我老伴起病之前就曾病了,送来宜昌诊治,需要做手术,医院认为她年岁大了不给做,他们便回去了,算来已经是五六年了,现在依然好好的。这次我见着,精神非常不错,还在厨房忙着。二姨他们夫妇,春节是在重庆过的,也在给儿媳帮忙,大儿子在重庆有份事业,儿媳也在做着生意,二姨他们在重庆显然是过得满意,这次回来了,仍然还津津乐道着重庆的故事。三姨的儿子在北京,儿媳在许昌,就两老在家里,他们把家里打理得很有条理,新起了房子,田园里,鸡舍里,他们都舍得下功夫,每年,他们都会给我们送好多好多土鸡蛋来,我的女儿很惊叹,夸说:“三姨妈她们的鸡子真肯下蛋。”我的老伴病危之前就曾在三姨他们那儿玩了半个多月。舅弟是最小的,也是精力最旺盛的。还兼职做着好几份事,手艺也是最多的。这次到乡下去,进村的路正在修,車开不过去,我们绕了老大一个圈,一看进村的路也是封着在扩修,过不去,没办法,还是舅弟骑着摩托来接我们了,上了一条旧时土路才进得村去。他儿子在武汉边工作边读研,还想读博士,他们都非常支持。虽然大家都渐渐老了,但家境都还好,精神也好,很是让人高兴。
乡村里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时令也快到“人倍忙”之时,油菜籽渐渐黄了,麦穗也渐渐黄了,这是丰收的象征。自然我们的话题除了家常之外,也多在农事之中。田里有收成,会给他们带来些收益的。这是传统的经济来源。大家也都盼着。“大风吹不断牛尾巴”,但愿老天能够眷顾吧,送给他们一个满仓的收成。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屋旁的那口野水塘,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好处,他们没在塘里放养过鳝鱼,但野生鳝鱼不少,也没在塘里放养过龙虾,而龙虾成群。每晚他们都会用网去放收龙虾,用毫子去放收鳝鱼。舅弟是绝对的行家里手,捞鱼摸虾成了他的兴趣爱好。这种土龙虾土鳝鱼,是人们.舌尖的美味,每天都会有人上门收购。他们坐在屋里,不经意间,已有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哩。他们告诉我,这些天,卖龙虾和土鳝鱼的收入已快接近去年全年种植棉花的纯收入,多可观呀!我有兴趣去看了看那野水塘,杂草丛生,浮萍满池,显得非常原始。而且,荷叶已有了尖尖角,过不了多久,荷花要开了,莲蓬要结了,那又是一种时尚美味呢,自然也会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他们也会享受那难得之风情的。听他们描绘着这情景,真是开心的。
妻兄弟和姨妹都是好客的,自然他们是用了最好的且是最“土”的菜肴招待我们了,宰了土鸡,杀了土鳝鱼,煎了土鸡蛋,蒸了龙虾,还有新剥的青豆,刚摘的生菜,现拔的莴笋,土土的,纯纯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土“得不要不要的,是“绿“得不要不要的。满满一桌子,让我们享用了。谁若说这不是最原生态最环保的,那就怪了。浓浓的亲情就在这土味中烹调着生发着。我们品味着,享受着,人是快要醉了!醉在这土土的乡情里!
而且,我们走时,还带走了满满的土货哩!土腊蹄,土鳝鱼,土鸡蛋……真的,小車的后备箱都装满了。他们恨不得倾其所有,全部让我们带回。这份情意太让人感动了。是的,我们带走了这土土的乡情,带走了这乡下的风物,带回了妻兄弟姨妹妹们那淳朴而深厚的情意!我们又怎么能带得够呢!它有如那散发着清香的泥土,催熟着麦苗和油菜的籽实,把丰收的希望写在无边的旷野里,写在大家的心上。是的,我也只能把这份情缘记在心里,让它伴着土土的乡情扎根,抽长,而成为我余生一道最美丽的风景吧……
是夜,又得《长相思》一阙,也记录于此了:
麦子黄,
菜籽黄。
五月农家正欲忙。
新荷出水塘。
说里短,
话家常。
土味舌尖情意长。
行车尽带香。
(年5月2日夜写于宜昌半岭居)
我在花海,有朋远来
我在花海。是因为“有朋远来”。
今年,枝江市同心花海的樱花节是3日23日拉开序幕的。这天,我没有去,而是第二天我到了花海。是的,又是去了一趟同心花海,但这是一次不在计划内的出游。
也就是昨天,我在武汉的大学同学志农给我来电话,说他与他河南郑州的几位好友今天想来同心花海一游。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到,同心花海的好多文化创意和文化元素都是学兄吴教授帮的忙,满是他的心血。得去看看他的成果和杰作。想一想吧,武汉市到枝江的同心花海,公里的车程,就为了到一趟同心花海,此情多可贵呀!这样,我不得不赶去了。大家可想而知吧,人家大老远的从武汉来,还有外省的朋友,我不去恭迎像话吗?自然得赶去啊!清早,我就从宜昌出发,赶到了花海。我对他们说“我在花海,等你们远来!”
花海的王总玉梅妹子听说我和朋友们要来,很给面子呀,安排得很到位的,并且在百忙之中和朋友们一一见了面。让朋友们很是感激,因而也玩得很尽心。花海是昨天樱花节开节,游人简直爆棚,多游客,几次出现游客人数超量的报警。这是过去不敢想像的一个数值呀!在那儿演出的青龙山农耕艺术团的曹礼圣会长对我说,一天下来,他们的演职员们累的人都不行了,用于表演的打硪杠打断了好几根,竹竿舞的竹竿跳破了有几抱,可见一斑了。今天的游客依然爆满,来的车没位置停,只能沿枝(江)当(阳)公路边线摆放,摆出一、二里路来。
花海经过去冬今春的扩建改造,又变了一些样子,樱花园内修了水塘,增加了迭瀑,增架了水上木桥,修了穿园路道,另外,还修了个门楼,这一来,既增加了情趣,也分流了游客,大家赏游起来更可悦心了。我的朋友们对那些临水而开的红白相间的樱花是十分的感兴趣,武大有樱花,但武大的樱花不傍水,这里有花有水,花亲水,水映花,味道足。他们说,这花海要是离武汉还近点,真是不得了呀!他们说的很真诚,我信。过去,人们经常埋怨,说平原之地不好做旅游,可同心花海这几年把农与旅结合,把花与文结合,把游与学结合,把玩与食结合,慢慢地摸出了些门道,做出了兴趣,也做出了信心。自然,客源是越来越广,加之交通方便,大家都愿意来这儿感受春的气息,来沐浴花的芬芳。我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了,他们在樱花树下,在菜花丛中,在郁金香处照了好多好多照片,照得都不想离开啊!
“有朋远来”,我作为东道主,是不能没有心意的。今天,我到花海去,给我的朋友们还是带去了一点小礼物的。给郑州来的朋友们每人送了一本我的拙著《竹海那方情》,这书是去年春出版的,礼轻情意在吧,我还慎重地签上了“同心花海”字样,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纪念了。这书,我曾送给志农学弟一本,再送就没意义了。送什么呢?我费了点心思,昨晚给志农现作现书写了一副楹联:“志以勤耕多乐事;农当富廪满欣情",这是副藏头联,今天送给了他,是情意,也是共勉吧。而且,这副联在花海相赠,还真是别有意义。花海所在地问安镇,是关庙山遗址所在地,关庙山遗址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年前,我曾送给问安镇一副联,为:“农耕有史读关庙;楚韵多情品问安”,就说到问安的两大文化特点,农耕居其一,而今天送给同学志农的这联,“农耕”也是主要内涵啊!在这儿相赠不是显得更合拍吗?看来,志农学弟还是比较满意的,中午进餐时,赠予他,即刻留下了合影纪念。
自然,这次去也给花海带了一点东西去,一是为他们即将辟建的楚辞植物园做了一副对联:“沐楚风会心辞韵;知卉草钟意自然",春节前就议到了这事,而对联做好后一直没机会送去,今天正好到了花海,赠予了他们,也算是自已的一点表示吧。同时,昨天晚上还书写了一幅字:“花之仙“,也是为他们的景点而书的,园区内还须要这样的东西。多一些这类的东西就多了一些拍照点,自然,也会增加游客的兴趣。故乡的建设,花海的发展,是需要众人相助的。“何人不起故园情”?作为游子,更得为家乡助力!
离开花海时,我们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最多的当然是花香。出园时,几位朋友身上满是花瓣,黄的是菜花瓣,红的是樱花瓣,白色的除了梨花瓣,也是樱花瓣,起初大家都没在意,只顾游览得尽兴,可这时一见,满身都是花瓣,他们都笑了:“我们把花海的花瓣都带走了!”在园区出口处,一值勤朋友也接话了:“这蛮好呀!把我们花海的色彩都带回吧!把生活过出颜色来!”而我带回来最多的却是照片,是花海的高颜值!是无比悦心怡情的春色!自然,也有花海和朋友们的那份真情!是用花蜜酿出的真情!
太阳西沉时,朋友们离开了花海,向着武汉驶去。分别时,朋友们真诚地对我说“花海真不错!我们还会来的!”
是的,朋友,来吧!再来共享这“美”的大餐!
是啊!“有朋远来”,我依然会等在花海……
正是春风柳色新
友朋远至品同心。
拳拳花海芳香漫,
半沐金黄半沐殷。
一一花为仙,情为魂
(年3月24日初稿,年8日2日整理)
故乡的黄花梨
侄子们从故乡来,带来了故乡的黄花梨,一袋一袋的,滚圆滚圆而又沉沉的,这正如我的乡愁,是那么殷实而又多感。侄媳还说,为了能给您们多带点来,清晨五点多钟就起床去摘梨子了,这更让我感到了这梨子的份量,这乡愁的厚重!这乡愁的淳朴和率真!
梨,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是有着另一种意义的,正如“橘”,通“吉”,人们是喜欢的,总是盼望着与“吉”相伴,一生吉祥;而“梨”谐“利”,自然人们也是看重的,总盼望着“大利”相随。东汉时期的孔融,那让梨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是熟悉的,这故事之所以能留传于今,这其中,除了人们能看到道德的力量外,还让人感受到了那“让利”的大度。不然,这故事是无法千古以承的。
从我记事时起,我们的老家是不种梨的。关于果木,我们的老家有一条俗谚:桃三李四杏五年,枣树当年能卖钱。谚中说了这么多水果,竟然没提到梨。可见梨于我们故土而言是陌生的。那些年我在乡下,正是割“尾巴”的岁月,谁家养的鸡多点,便会被责令杀掉。果木也是一样,命运都不会好,砍的砍了,挖的挖了。我们诺大一个村落,就见着沮漳河边我一位远族的长兄门前有一棵枣树,大概是因为这树有着几十上百年的缘故吧,“割尾巴”的人手下留情了,还没有被“割“去,以至于枣子熟了,便成为了孩童们的乐园。尽管枣枝有刺,大伙儿还是乐呵呵地打着枣儿:打枣枣,打枣枣,打多多,打少少,左菏包,右荷包,装鼓鼓,快点跑……这些枣子也是不允许去卖钱的,主人也便看着孩子们开心地玩耍。
当年,我们的老屋后,不知何时也生出来了一棵柚子树,慢慢的,七八年了,也长得像一棵树了,猴模狗样的,但是它就是不挂果,不知是天不时,还是地不利,或者说它也通人性吧,是不是一旦挂果,便担心着被“割”去呢?后来分田到户,这时的我们是离开了老家,但乡亲们后来告诉我们,那棵柚子树真的挂果了,味道还真不错的。这真怪了!是天时了,是地利了?是赶上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时光吧!
当年在乡下时,种植是单一的,春种麦,夏种棉,这是铁定的,谁也改变不了。后来是真变了,乡亲们可以自由选种了。多种经营也便发展起来。桃子有了,李子有了,这些年,梨子也种植成功了,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眼前的这些梨子一一从故乡来的黄花梨是最好的佐证啊!这是带着乡亲的心愿来的,也是带着祝福和期盼来的。看一眼,实甸甸的;咬一口,清脆脆的,真让人感慨万端呀!大家一定熟悉这两句诗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用梨花来写雪花的,写雪花粉嫩,飘忽和晶莹。倘若反过来呢,用雪花来写梨花呢?那不是更美吧?悠然间,我似看见春风中梨花盛开的景象,那种飘逸,那种雅致,那种珣丽,真可醉倒千万人的。一下子,也似乎让我回到了一个甲子前,在沮漳河畔,在柳树林中,有着采摘野藜蒿一样的欢欣,说不定再入这梨花的天地,还会演出一场“郎骑竹马来”的儿童大片哩!现在正是梨子成熟季节,在那累累果实之下,你会不会去寻找“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韵味?我想像着,那应该是乡亲们最幸福的时光!
故乡的黄花梨是丰收了!百亩千亩,那一定是果实的海洋,是大利的天堂。谁说“雨打梨花深闭门”?我知道,故土早已敞开胸怀,张开双臂,笑迎着八方宾客。我们自然有理由,去分享他们丰收的喜悦,去分享他们利好的时光!黄花梨,这是时代的红利!
硕果盈枝七月鲜,
乡愁甸甸压心田。
吉祥岁月承天利,
情满沮漳水更甜!
是啊!再次品尝黄花梨,我品出了别样的乡愁!
(年7月29日于宜昌半岭居)
《夷陵评论》欢迎惠赐达到省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水平的文学作品,来稿附个人简介、个人照片,邮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