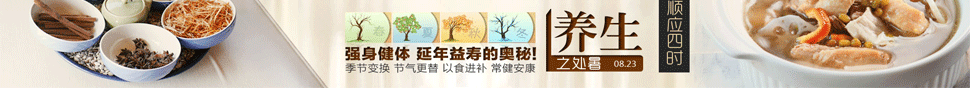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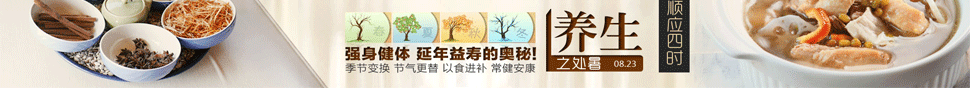
鲤鱼山的荏苒时光
文/王选玲
珊溪鲤鱼山是一座高约40米,长约米,宽约50米的小山包。它位于珊溪水库大坝的坝脚,从谷歌地图俯瞰,它像一颗梭形的绿宝石,镶嵌在屋瓦丛中,更像一条搁浅了的草鲤,鱼嘴朝西,鱼尾朝东,无奈地趴在珊溪口的飞云江畔。
鲤鱼山上生长着各种树木,有竹子,有杨梅,竹子和杨梅的间隙里还长着各种各样的杂树硬柴。山脊背上缺水少土,长不成竹子和树,就被农人开垦种了青菜,中间一条小路,都是风化了的白砾石。这条白色的鱼脊,俯瞰就像上了年纪的中年人头顶那片“地中海”。
菜园中间竖着一块石碑,据碑上记载,鲤鱼山曾出土过石刀石斧等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这些文物,把鲤鱼山的历史从国民党建碉堡打共产党的近代史,一下子拉伸到了几万年前的上古时期。
摘公公、采桑叶、找竹叶米、拔小青、折山蕨、挖红薯、挖笋、抓小鸟、赶山鸡、拔草、捡枯树枝、笆松针......
记忆里,鲤鱼山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宝藏。
有一次,也仅有一次,我与小伙伴们一起到山上偷摘茶叶,那时候鲤鱼山上没有杨梅树,却种满了茶树,茶树属大队所有,私人是不能采的。我跟着小伙伴去偷摘茶叶,只是图个刺激好玩,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茶叶摘过来干嘛用的,结果被人发现了,几个小伙伴手里拿着装了一点点茶叶的小塑料袋,从山顶飞也似地逃下山。我们并没有因为没偷到茶叶而沮丧,更没有因为偷摘茶叶而倍感丢脸,有的只是偷摘时提心吊胆的刺激,和飞逃下山后取笑彼此狼狈相的捧腹不禁。
鲤鱼山脚下有个村庄,叫屿后村,即岛屿后面的村子,以前那里没几户人家,不能称之为村,我们称它屿后坦。
二三十年前,屿后是溪滩野,只有靠着山脚住着若干刘姓村民,他们是同一祖公派下的一家人,彼此之间以叔伯兄弟姊妹相称。那些年,屿后是一栋一栋单门独院的泥墙屋,前有田坦,后有杂院,每家院子里都会种着桃树、梨树、芭蕉树、板栗、桔子树、柚子树、李子树、杨梅树、石榴树、葡萄等当地果树,免得别人家的孩子有零嘴吃,而自家娃娃哭闹着要。泥墙屋大小不一,形状不一,前后错落,一栋与一栋之间由青石和鹅卵石拼筑的小路相连,整个村子掩映在高大的溪构树(学名枫杨树)丛中,溪构树下自由地生长着各种山棉花、鬼针草等灌木杂草。
前几年,我跟朋友到杭州灵隐寺后山的法云安曼走了一圈,法云安曼大小错落的泥墙屋,以及小溪边的溪构树坦和树下各种自生自灭的杂草,依稀之间,是那么的似曾相识。今天在这梳理文字,才突然想起,那竟然是我儿时对屿后的印象。
屿后村外面是沙地,勤劳的村民用溪里的鹅卵石把沙地筑成一块块的菜园子,菜园里种着各种时令青菜。到了种麦子的季节,沙园子里就会全部都种上麦子。
“噼噼啪!噼噼啪!大家来打麦。
麦子多、麦子好,磨面做糢糢。
糢糢甜、糢糢香,以前地主吃,现在自己尝!
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一首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麦子童谣,道尽了上个世纪大家对麦子熟的向往。磨面做糢糢我小时候已经没有印象,但磨面做拉面,那仿佛过大年一样的兴奋,却是我们那一代人童年里最深刻的记忆。
现在这些青青的麦园和园子外面的溪滩野都已经被开发成了洋房,一排排贴着白色墙外砖的洋房,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刺眼的白光。
屿后村出去,沿着山脚一直到鲤鱼山尾,那一带以前都是溪构树坦,都是没人住的,可算得上是珊溪的荒郊野岭了。浓密阴凉的溪构树坦,是附近孩子们避暑纳凉的最佳胜地,更是我等娃儿们游戏捉迷藏的最佳去处。
每年做大水,暴涨的飞云江和珊溪水都会给这两江交汇的溪构树坦涨来厚厚的沙子。我们可以在软软的沙地里挖坑做陷阱,可以抓蚱蜢,可以在顺着山脚脉脉而淌的溪坑里用毛巾和泥箕撩小鱼,撩虾米。我们也经常会躲在溪构树坦的某一处,远远地望着来自街尾村的大男孩在树林里“嘿哈!嘿哈!”地练功夫。在树荫下的沙地里练功夫,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练功场所了。
我们有时还会猫着腰在树坦的灌木丛里穿梭,寻找那些躲在树坦里谈恋爱的男男女女们,恶作剧地吓他们一跳,然后哄笑着四散逃窜。
这片收藏着儿时无限天真的溪构树坦,现在依稀还留存着些许模样,飞云江广场原生态的绿化带里那些高大的溪构树,就是当年溪构树坦的残存。
图片来自网络
?E·N·D?
声明
本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ouzishua.com/yzszp/62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