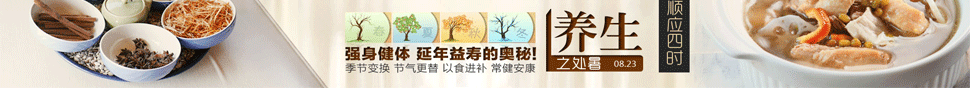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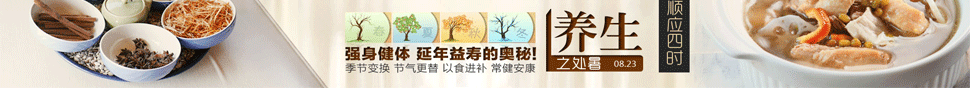
作者:龚晶晶
“你,听到过大黄鱼的叫声吗?咕咕咕咕……50多年来,那声音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走访时,当年捕捞大黄鱼战功赫赫的船老大们多已年近暮年。他们说,多可惜啊,儿孙们,都不曾听过东海边上大黄鱼的歌唱。
你看,人就是这么矛盾且可笑的动物,我们用10年时间,让野生大黄鱼绝迹于东海。却用余下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怀念那个能在海风里听见大黄鱼叫声的五月。
只要提起大黄鱼,老一辈的象山人总有说不完的回忆。
在他们对大黄鱼的口述中,爵溪,是一个绝对不能跳过的地名。
象山之北,有镇名为爵溪。昔为渔村,因村南一溪林茂噪,故名“雀溪”,元代谐音作“爵溪”。三面环山,东频大目洋。世代捕鱼为生,清时已蔚成渔埠。清末,捕大黄鱼之量居浙洋前列,所产“爵鲞”为朝廷贡品。
渔汛时,沿海各省千帆云集爵溪,桅樯林立、帆影叠嶂、渔光交错,蔚为壮观。爵溪滩头,鲞厂百余家,盛时产鲞2万担(吨)。因黄鱼鲞色白、味美,远销各地,久负盛名。
“50多年前,每到3月半至5月半的春夏渔汛,爵溪的大黄鱼就多得不得了,丹城等地的很多人都会翻山越岭地去爵溪挑黄鱼。箩筐里一条条几斤重的大黄鱼用山上的橡树叶盖上,挑回丹城还新鲜得很哩。”现年67岁的爵溪镇原镇长郑根兴告诉笔者,由于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冷库等保鲜设施,挑走的大黄鱼数量极为有限,大量的大黄鱼只好在爵溪就地处理成白鲞。
可惜到了20世纪60年代,爵溪渔民赖以为生的大目洋渔场,因大黄鱼产卵期与捕捞同时,闽海渔船大量北上,渔船设备日益先进,捕捞量大增,大黄鱼资源枯竭。加以舟山渔民开辟大沙渔场,使大黄鱼渐失越冬场所。至60年代末,爵溪渔业一蹶不振。
“尤爱郎君(爵鲞别称)风味好,美鱼珍重爵溪名。”旧时名句,如今想来确是引人叹惋。
象山爵溪大黄鱼日渐式微的60年代,却是舟山岱衢洋一带大黄鱼捕捞的黄金时期。
问及此事,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原副局长陈员祥抿了口茶,开始陷入回忆。
年,陈员祥出生在舟山岱山的一个小渔村,毗邻昔日威名远播的大黄鱼主渔场岱衢洋。他记得,儿时每到农历4、5月间,寂静的夜里,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黄鱼叫声。“咕咕咕咕”,夹杂着海浪击打礁石的声响,伴他入梦。
彼时的他,年岁尚小,只一心记挂着,若是夜里海上挂起大风,明早一定要抢先去海边捡些大黄鱼回来。哪里晓得,正在他酣睡的当下,无数悬挂的帆蓬正潜伏在岱衢洋的海面,静候大黄鱼的光临。有经验的渔民总会附身趴在木帆船的船舷上,顺着大黄鱼的叫声,判断鱼群大小、密度甚至深浅,而后进行捕捞。
那时,村人常能望见:江、浙、闽等地的捕鱼船只密密麻麻挤在一处,夜间白炽的照明灯灿然若昼,“岱山十景”之一的“衢港灯火”由此得名。可惜,如是景象,在此后十余年间,终是随着大黄鱼的消失,成为后人只可神往的“陈年旧梦”。
"楝子开花石首来。"宋人范成大有诗如是写道。每年春末夏初,楝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易。谁也想不到,有一天楝树空自开花,黄鱼不来。
在陈员祥的回忆中,上世纪50年代,浙江一带的渔民开始学习福建进行敲罟(gu,音鼓,系方言音译)作业,确认鱼群位置后,许多船会一起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合音,声波传入海中,使得大黄鱼这样的石首鱼科鱼类耳石共振,昏迷死亡。
据相关资料记载,年春汛时,浙江渔民大批量使用敲罟作业,捕捞的大黄鱼总产量达到了常年的20余倍。鱼多价贱,大黄鱼跌至每斤五六分钱,更多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
敲罟作业成本很低,效率极高,凡石首鱼科鱼类,不分老幼,一律聚歼,堪称解决大黄鱼的终极渔法。
不久国务院发出指示,把敲罟作业作为"一种有害渔法"加以禁止。然而"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许多地区又恢复作业,致使大黄鱼的沿岸产卵群体受到严重破坏。
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年的初春,浙江省组织了近对机帆船前往大黄鱼的主要越冬场外海中央渔场围捕。这一年渔发面积大,鱼群密度厚,舟山渔场的大黄鱼产量由10万吨猛增到16.81万吨,创造了我国渔业史上大黄鱼产量的最高纪录。
“自此以后,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一蹶不振,销声匿迹。”几乎所有报道都于此处戛然而止。所幸,走访中,更多不为人知的渔人往事,在亲历者的口述里,渐渐浮出水面。
年,初五。
夜色渐沉的海上朔风凛冽,一艘写有“宁渔”字样的渔船悄然停靠在了舟山嵊泗列岛一带。“我们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本来打算北上,前往黄海与渤海湾之间的海域捕捞青鱼,谁想到半路船抛锚了。”这艘船上的轮机长就是此前故事里的舟山小伙陈员祥。
初六零点,检修完毕,“宁渔”继续北上。一船人都有些疲惫。
可到了凌晨3、4点钟,途径海区时,垂直鱼探仪上的一块影像,引起了船员的注意。
船长贝章财是当时宁波赫赫有名的老船长,出海经验很是丰富。他看完后,笑着对大副说:“那就下一网试试,就当给大家添点小菜。”这一网,满满的鳀鱼里,夹着几条少见的大黄鱼。
热闹过后,天色已亮,“宁渔”继续一路向北。
初七零点,已经睡下的贝财章突然被人慌慌张张地叫醒。原来,值班大副在垂直鱼探仪上又发现了一块奇怪的影像。“与第一次黑且密的影像不同,这一次的比较疏散,就像毛笋一样,出现在距离海底25米的位置。”
“放网!”贝财章当机立断,下达命令,“宁渔”开足马力向鱼群包抄,长达米的渔网从船尾吐出,底钢缓缓下沉。不到5分钟,网船与随行的2条灯光船合拢,鱼群被围困在网圈之中。
渔网的浮子在深蓝的海面上,画出一个直径米左右的包围圈,陈员祥爬上驾驶台顶,用探照灯一照,只见平日里白色的浮子此刻却犹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再定睛一看。“不得了了!全是大黄鱼!”所有人都沸腾了。
随着吊杆的升起,几分钟后,网圈里密密麻麻的大黄鱼开始如海水般涌出水面,因为鱼实在太多,深达米的渔网根本无法起网,哪怕是在海上见多识广的贝财章也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景。
船员们只能坐上舢舨,用篰一趟又一趟地打捞大黄鱼,寒冷的冬夜,每个人都忙得汗水涔涔。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整艘船完全装满,也只是捞完了冰山一角而已。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6点半,太阳从海岸线升起,海面上一片金光闪闪的样子。”在陈员祥的记忆中,那天他们一共打捞上吨大黄鱼,箱装的满满当当,但渔网里还是留有不计其数的大黄鱼,沉得无法收网。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割破渔网,让鱼顺流而出,一时间,方圆几公里的海面,全都漂浮着金灿灿密密麻麻的大黄鱼。
上午8时,“宁渔”上的报务员向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渔捞科发出电报,汇报现场情况,并请求其他5组已经北上的船只返回同一海域捕捞大黄鱼。结果,返航船只,尽数满载而归。
这无疑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捕捞大黄鱼史上的一次大捷。
“此后,每年2月至5月期间,我们都会大部队来到该海域捕捞大黄鱼,当时不少群众的机帆船也会跟着我们的围网船出海,没几年,大黄鱼就越来越少了。到80年代初,大黄鱼已经无法形成渔汛,也再没有人过进行专门的大黄鱼捕捞了。”如今已经退休的陈员祥,再回忆起那短短十余年的海上生活,叹了口气,不胜唏嘘。
在七八十年代的东海,除了大型的围网船,海上最多的就是老百姓的机帆船。船上的船老大多是祖祖辈辈捕鱼为生,问及故乡,石浦东门渔村,便成了出镜率最高的地名。
全国渔轮看象山,象山渔轮数东门。走访中,笔者发现在这个与石浦镇隔海相望的“浙江渔业第一村”里,也藏有许许多多未曾被记载过的大黄鱼传奇。
彼时的船老大不少已经故去,余下的多也年近暮年。他们说,当时东门岛渔人的足迹,已经踏遍大目洋、猫头洋、渔山岛、大陈渔场,由于鱼类减少,他们只能去遥远的外海继续讨生活。生涩难辨的方言里,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海上传奇,被时间浸泡成了一帧帧定格的黑白默片……
年,外海渔场(今海区,水位42米),船号、。象山东门渔村的带头船老大杨师傅,就曾一网捕上过10万斤大黄鱼。后,在同一位置,另一船老大葛师傅一网捕上8万斤大黄鱼。
年,东门渔村船老大吴昌龙,驾一木帆船,于衢山考门(方言)与铁灯江(方言)交界处,以毛竹打桩,捕获8万多斤大黄鱼。(“考门”、“铁灯江”这两个地名笔者均未从地图找出,只能以方言谐音记录,还望知情读者留言告知。)
年,檀头山与鸡笼礁东,船号。东门渔村船老大冯永纪,拖网捕获3万多斤大黄鱼。
年,将军帽岛以东,船号。东门渔村船老大金祥根,于农历四月初九及四月十九,两网共拖网捕获5万多斤大黄鱼。
年,渔山岛东南,船号。东门渔村船老大许良清,拖网捕获3万斤大黄鱼。
……
可惜,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是伴随着消失的大黄鱼,一起湮没于大海深处。
“等我19岁第一次出海的时候,已经很少能捕到大黄鱼了。”现年63岁的东门人梅岳明拥有24年的捕鱼经历,但最难忘的还是首次出海的情景。
那是年农历四月初的一天,彼时的机帆船都跑的极慢,他坐着那艘马力的渔船,在海上漂了整整30个小时才抵达海区。由于早年间在小船上摇撸的经历,这样漫长的航行,梅岳明早已习以为常。那一次,他们很幸运地捕到了1万斤大黄鱼,“1毛5一斤。”价格他到现在都记得分明。“哪像现在,市面上4斤的野生大黄鱼都能买到上万元一斤了。”
后来他才从有经验的渔民那里得知,年至年期间,檀头山一带还有很多大黄鱼,只是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梅岳明成了岛上第一代个体户,同妹夫一起承包了2艘4米5的渔船,而当时,全象山仅有8对船,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千鱼万鱼,都比不上大黄鱼啊。”在24年的海上生活中,大黄鱼,就像是萦绕在老梅心里的一个梦。而这样的梦也真真切切的存在在每一位亲历者的心中。
故事讲到这里,或许,你会问我,东海野生大黄鱼都已经被灭门了,后面还会有和它相关的故事吗?
当然,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年,捕了24年鱼的老梅成了东门岛上第一个养鱼的人。此后的19年里,他养的最多的就是大黄鱼。
7年,在时任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原副局长陈员祥的支持下,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专门成立了“野生岱衢族大黄鱼采捕”攻关小组,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岱衢族大黄鱼(东海野生大黄鱼的学名)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的战役。
此前,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根兴及他的团队,已成立了浙江省第一家岱衢族大黄鱼育苗基地。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的岱衢洋大黄鱼野生亲本采捕、保活、繁育和种质库建设项目。至今已成功繁育出岱衢族大黄鱼苗种2亿2千多万尾,为全省人工增殖放流岱衢族大黄鱼苗种提供保障。
截至目前,老郑的公司共放流岱衢族大黄鱼超过1亿万尾……
在象山、在宁波、在中国,还有无数人像他们一样,打算为了这一条大黄鱼,倾尽余生的全部心血。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咕咕咕咕”,
杂着海风,踏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咕咕咕咕”,夹杂着海风,踏浪而来……
浪而来……
明州世相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网络
爱我,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ouzishua.com/yzsfb/8990.html


